

阿Q正传
一个干瘪的身影,顶着几根稀疏的头发,在未庄的斜阳下晃荡。他刚被人扇了耳光,却能转过头去,心满意足地嘟囔一句:儿子打老子。这就是阿Q,一个连姓氏都被剥夺了的边缘人,在1981年这部同名电影里,被严顺开演活了。 故事发生在一个看似平静实则腐朽到骨子里的江南小镇。阿Q住在破旧的土谷祠里,靠卖力气打零工混口饭吃。他虽然穷得叮当响,心里却住着一个傲慢的君主。只要他在精神上把对方降格为孙子,现实中的拳头和唾沫就仿佛成了某种勋章。这种独创的精神胜利法,成了他在苦难生活中唯一的避难所。 原本他这种底层的小透明,只要安分守己,或许也能在冷嘲热讽中混完一生。可随着他试图向吴妈求爱被毒打,生活彻底脱了轨。为了活命,他远走他乡,却又在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时,阴差阳错地回到了未庄。 这时候的阿Q,腰间似乎别着了不起的秘密,连平日里高不可攀的赵太爷都对他露出了谄媚的笑脸。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那个改天换地的机会,以为自己也能去那朱漆大门里翻箱倒柜,甚至幻想着那些平时瞧不起他的女人都围着他转。可他不知道的是,时代的巨轮隆隆碾过,他这种自作聪明的小人物,究竟是弄潮儿,还是注定被碾碎的齑粉?
剧情简介
一个干瘪的身影,顶着几根稀疏的头发,在未庄的斜阳下晃荡。他刚被人扇了耳光,却能转过头去,心满意足地嘟囔一句:儿子打老子。这就是阿Q,一个连姓氏都被剥夺了的边缘人,在1981年这部同名电影里,被严顺开演活了。 故事发生在一个看似平静实则腐朽到骨子里的江南小镇。阿Q住在破旧的土谷祠里,靠卖力气打零工混口饭吃。他虽然穷得叮当响,心里却住着一个傲慢的君主。只要他在精神上把对方降格为孙子,现实中的拳头和唾沫就仿佛成了某种勋章。这种独创的精神胜利法,成了他在苦难生活中唯一的避难所。 原本他这种底层的小透明,只要安分守己,或许也能在冷嘲热讽中混完一生。可随着他试图向吴妈求爱被毒打,生活彻底脱了轨。为了活命,他远走他乡,却又在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时,阴差阳错地回到了未庄。 这时候的阿Q,腰间似乎别着了不起的秘密,连平日里高不可攀的赵太爷都对他露出了谄媚的笑脸。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那个改天换地的机会,以为自己也能去那朱漆大门里翻箱倒柜,甚至幻想着那些平时瞧不起他的女人都围着他转。可他不知道的是,时代的巨轮隆隆碾过,他这种自作聪明的小人物,究竟是弄潮儿,还是注定被碾碎的齑粉?
播放线路
观影点评
如果说鲁迅的原著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,那么这部电影就是一面被擦得锃亮的哈哈镜,映照出人性深处那些荒唐又可悲的褶皱。严顺开老师的表演简直是神来之笔,他那双闪烁着狡黠、卑微又带着点狂想的眼睛,把阿Q那种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状态拿捏得入木三分。 这部片子最妙的地方在于,它并没有把阿Q塑造成一个单纯的受害者。他在强者面前奴颜婢膝,却在更弱小的小D面前趾高气扬。他那种精神胜利法,就像是一种廉价的麻醉剂,让他能在烂泥地里自封为王。电影用一种带着黑色幽默的调子,把这种病态的国民性剥开给人看,让人在发笑之余,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刺痛。 看电影的时候,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很奇妙的情绪里:前一秒还在为他的滑稽举止发笑,后一秒就会被那种透骨的凄凉冻住。尤其是最后那个画圆圈的场景,那是阿Q这一生最后的体面与挣扎,他拼尽全力想画得圆满,却终究只能留下一个歪斜的遗憾。 这不仅仅是一个旧时代的故事。当你看到阿Q在被生活毒打后,依然能通过一种逻辑自洽的自我安慰获得快感时,你会惊觉,这种阿Q精神其实从未消散,它只是换了身衣服,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。这可能就是经典的力量,哪怕过了四十多年,它依然能精准地扎中现实的痛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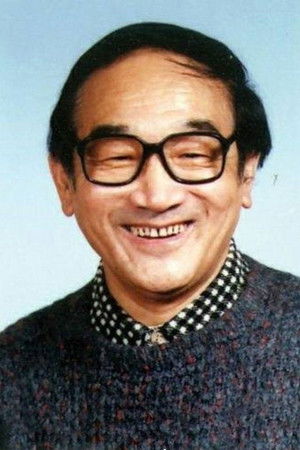



 0
0 0
0 0
0 0
0 0
0 0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