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人生七部曲
一个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领着几十个孩子,在简陋的屋子里载歌载舞地歌颂精子的神圣,转头却因为养不起而要把他们送去搞医学实验。与此同时,对门的新教邻居正翘着二郎腿,一边嘲笑这种狂热,一边庆幸自己只做了两次爱,精准地生了两个娃。这就是这部电影给人的第一冲击,它把那些被世人奉为圭臬的信条,像拆积木一样拆得稀碎,再堆成一个荒诞不经的怪谈。 这部作品由传奇的蒙提·派森团体打造,他们野心勃勃地试图用七个章节来拆解人的一生。从呱呱坠地时的手术室狂想,到学校里那场由教授亲自上阵示范、尺度大到令学生目瞪口呆的性教育课,再到战场上士兵们在炮火连天中非要给长官办一场体面的生日宴。它不讲什么温情脉脉的成长故事,而是用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,把人性的贪婪、虚伪和迷茫剥开给人看。 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那个关于死亡的章节。当死神披着黑袍敲响农舍的大门,本该是肃穆而恐怖的时刻,结果屋里那群正在聚餐的美国人不仅没被吓破胆,反而像招待远房亲戚一样,拉着死神喝酒聊天,甚至还要和他探讨社交礼仪。这种极度错位的张力贯穿始终,每一段故事都在你以为要看懂的时候,突然来一个让你措手不及的神奇拐弯。
剧情简介
一个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领着几十个孩子,在简陋的屋子里载歌载舞地歌颂精子的神圣,转头却因为养不起而要把他们送去搞医学实验。与此同时,对门的新教邻居正翘着二郎腿,一边嘲笑这种狂热,一边庆幸自己只做了两次爱,精准地生了两个娃。这就是这部电影给人的第一冲击,它把那些被世人奉为圭臬的信条,像拆积木一样拆得稀碎,再堆成一个荒诞不经的怪谈。 这部作品由传奇的蒙提·派森团体打造,他们野心勃勃地试图用七个章节来拆解人的一生。从呱呱坠地时的手术室狂想,到学校里那场由教授亲自上阵示范、尺度大到令学生目瞪口呆的性教育课,再到战场上士兵们在炮火连天中非要给长官办一场体面的生日宴。它不讲什么温情脉脉的成长故事,而是用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,把人性的贪婪、虚伪和迷茫剥开给人看。 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那个关于死亡的章节。当死神披着黑袍敲响农舍的大门,本该是肃穆而恐怖的时刻,结果屋里那群正在聚餐的美国人不仅没被吓破胆,反而像招待远房亲戚一样,拉着死神喝酒聊天,甚至还要和他探讨社交礼仪。这种极度错位的张力贯穿始终,每一段故事都在你以为要看懂的时候,突然来一个让你措手不及的神奇拐弯。
播放线路
观影点评
看这部电影的过程,就像是在参加一场由疯子天才们主持的哲学派对。它那种典型的英式冷幽默,带着一种不顾他人死活的尖锐,把宗教、战争、性和死亡这些沉重的大山,统统变成了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。它不仅仅是在搞笑,更像是在用手术刀精准地切割社会那些道貌岸然的脓包,让你在爆笑之余,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通透。 导演特瑞·琼斯和特瑞·吉列姆将那种超现实的视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。你会看到像山一样肥胖的食客在餐馆里吃到身体炸裂,也会看到鱼缸里的鱼在讨论存在主义哲学。这些看似毫无逻辑的拼贴,其实构成了一幅极其宏大的人间浮世绘。它并不打算给你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标准答案,它只是想告诉你:如果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荒诞的闹剧,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肆地嘲笑它。 这绝对不是那种适合全家围坐、温馨赏析的合家欢,它是一剂猛药,专门对付那些对生活感到麻木或过度严肃的人。它粗鲁、冒犯、甚至有些恶心,但它内核里的那种自由灵魂和对生命的深层洞察,是任何正襟危坐的剧情片都无法比拟的。如果你已经厌倦了那些陈词滥调的人生哲理,一定要看看这出华丽而疯狂的众生相,它会让你重新定义什么叫作真正的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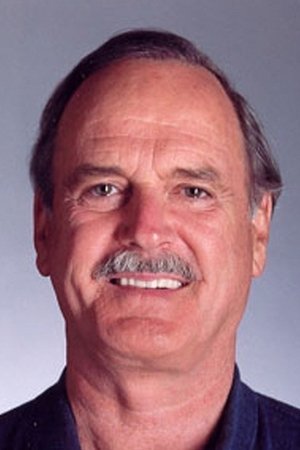

 0
0 0
0 0
0 0
0 0
0 0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