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血色浪漫
漫天大雪的什刹海冰场上,一群穿着将校呢大衣、戴着雷锋帽的年轻人正呼啸而过,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清脆刺耳。人群中,钟跃民那双透着痞气又藏着忧郁的眼睛,正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,是一个充满了躁动、热血与禁忌的特殊岁月中。 这群自诩为顽主的大院子弟,过着一种极其割裂的生活。他们可以在街头为了哥们义气拔刀相向,转头就能在昏暗的屋子里,伴着老旧唱机流淌出的柴可夫斯基,谈论着存在主义和远方的诗。钟跃民就是这群人的灵魂,他像一匹永远无法被驯服的野马,生活对他而言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体验。 当时代的巨轮开始转动,这群曾经在皇城根下无忧无虑的少年被狠狠地甩向了四方。有的去了黄土高坡,在贫瘠的土地上对着苍凉的信天游发呆;有的穿上了军装,在战火与硝烟中重塑脊梁。钟跃民与那个纯净如水的周晓白,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,却又在命运的岔路口面临最残酷的抉择。 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青春的往事,更是一场关于灵魂自由的漫长流浪。有人选择了安稳,有人选择了权位,而钟跃民却始终在路上,去寻找那个连他自己都无法定义的浪漫。在那个血色如画的年代,他们的青春被揉碎了撒在风里,却又在每一个转折点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剧情简介
漫天大雪的什刹海冰场上,一群穿着将校呢大衣、戴着雷锋帽的年轻人正呼啸而过,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清脆刺耳。人群中,钟跃民那双透着痞气又藏着忧郁的眼睛,正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,是一个充满了躁动、热血与禁忌的特殊岁月中。 这群自诩为顽主的大院子弟,过着一种极其割裂的生活。他们可以在街头为了哥们义气拔刀相向,转头就能在昏暗的屋子里,伴着老旧唱机流淌出的柴可夫斯基,谈论着存在主义和远方的诗。钟跃民就是这群人的灵魂,他像一匹永远无法被驯服的野马,生活对他而言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体验。 当时代的巨轮开始转动,这群曾经在皇城根下无忧无虑的少年被狠狠地甩向了四方。有的去了黄土高坡,在贫瘠的土地上对着苍凉的信天游发呆;有的穿上了军装,在战火与硝烟中重塑脊梁。钟跃民与那个纯净如水的周晓白,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,却又在命运的岔路口面临最残酷的抉择。 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青春的往事,更是一场关于灵魂自由的漫长流浪。有人选择了安稳,有人选择了权位,而钟跃民却始终在路上,去寻找那个连他自己都无法定义的浪漫。在那个血色如画的年代,他们的青春被揉碎了撒在风里,却又在每一个转折点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播放线路
观影点评
如果说大多数年代剧是在怀旧,那么这部作品则是在招魂,招那种独属于那个时代的、近乎偏执的理想主义之魂。导演滕文骥用一种极具张力的镜头语言,勾勒出了一幅宏大而又细腻的青春长卷。刘烨演活了钟跃民,他身上那种混不吝的痞气与骨子里的高傲交织在一起,让人既爱他的洒脱,又恨他的不羁。 这部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对浪漫的重新定义。那不是花前月下的呢喃,而是在极度匮乏和压抑的环境下,依然要保持灵魂高贵的倔强。剧中的信天游不仅仅是背景音乐,它是生命底色的呐喊,是这群特种钢在时代的熔炉里淬火时的嘶鸣。 钟跃民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,他追求绝对的自由,却又不可避免地伤害着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这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,让整部剧脱离了简单的青春偶像套路,具有了某种哲学思辨的深度。它告诉我们,那个时代虽然充满了血色,但那一代人的浪漫却是刻在骨子里的,是那种哪怕生活在泥淖里,也要仰望星空的极致浪漫。 看完这部剧,你或许会明白,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爱情总是那么刻骨铭心,为什么那份友情能抵御几十年的风霜。因为它不仅仅是在讲故事,它是在展示一种活法,一种不向平庸低头、永远热泪盈眶的生命姿态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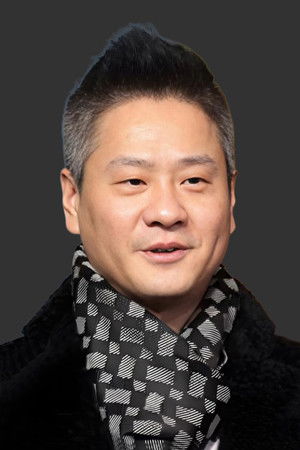




 0
0 0
0 0
0 0
0 0
0 0
0